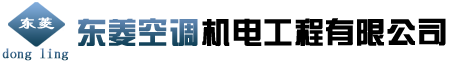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陳述詞
2018/11/20 8:42:38??????點擊:
首先,選題的過程及選題內容的確定。從我接觸我現在的學位論文選題的相關材料到最終確定選題的具體內容和時間劃限,我將我的選題過程大體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99年我入學之初到2001年6月我完成開題報告。實事求是地說,我的學位論文選題的確定,著實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為什么這么說?又為什么會這樣?這里我想先談一點有關我個人的學術背景。我是1999年考入東北師大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師從于群教授開始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而此前的本科階段和碩士研究生階段我學習的專業一直都是英語語言文學。1996年獲得碩士學位后我所從事的工作也一直都是與英語語言的教學有關。現在仍是如此,我是XX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英語專業的一名教師。毋庸諱言,我在歷史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是很粗淺的。僅憑著對史學的濃厚興趣、考博前在歷史系旁聽過一、兩年本科生課程的簡單學歷,和主要是由于入學考試英語成績名列前茅就獲得入學資格的幸運——我深知這些都遠遠不能幫助我完成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業。于是,入學之初,我就向于老師請教,請他給我布置選題,當時,于老師給了我FRUS(《美國對外關系文件》)中1964-1968年中國卷的電子版,并從這卷的347個文件中挑出了20個有關中國“文革”的文件讓我重點閱讀。同時,于老師也指示我可以從我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有關“文革”的情況,閱讀一些有關“文革”的中文書籍。但,當時做這些工作還只是想就美國對“文革”的認識、分析乃至對華政策寫一篇小論文。順便說一句,在這一階段(即入學的頭兩年)我實際上完成了這篇小論文的初稿,但由于那時我的思維習慣還沒有完全轉變到嚴謹的史學的邏輯思維上來,在寫作方法上也全然是個外行,所以這篇初稿一直處于修改狀態,當時并未投出發表。事實上,入學的頭兩年里我曾對畢業論文的選題有過些考慮,于老師也就我從事專業的實際情況出發為我做過一些設計,這期間于老師曾建議我利用10年的《紐約時報》作為第一手資料分析美國的對華認識,崔丕老師曾建議我做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這一選題后來我師姐王偉做了。),于老師還曾建議我做美國對英國的政策(這個選題已經畢業的張穎師妹做了。),這些選題或由于資料或由于我個人興趣的原因對我而言都無果而終。2001年春,我在梁茂信老師的大力推薦和支持下申請到去美國耶魯大學進行一個月的獨立研究的機會。有了這次寶貴的收集資料的機會,我和于老師商量決定把我一直在做的小論文做大,即把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作為我的畢業論文的選題。2001年6月,做開題報告時我把論文的題目定為“美國人的文革觀和文革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1966-1972)”。當時,開題報告做完,在座的老師們給我提的意見是,美國人的文革觀和文革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上是兩個題目。我覺得老師們說得很在理,但在這兩個各有傾向和偏重的選題的取舍上我始終拿不定主意。2001年6月到2002年春是我選題過程的第二個階段,應該說這一年里我一直在前面提到的兩個選題的取舍問題上徘徊,收集、閱讀和整理的資料也是兩者兼顧。2002年年初于老師去美國做高訪,回來后又幫我帶了一批在國內難以查到資料,并最終幫助我做了決定,論文主要做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2002年春到2004年春是我論文選題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嚴格講,此時我的選題大方向已經定下了,就是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我嘗試把美國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做一個系統的考察。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國人的算法是從1966到1976,即所說的“十年浩劫”,美國對“文革”十年的中國的研究從涉及的領域上講,可以說是系統且全面。關于這一點,從美國已經出版的幾本有關文獻目錄中也可窺其一斑。我嘗試把從1965年“文革”爆發前,美國人的對中國會出現某種重大的變化的預測到“文革”結束將近30年后,此間近40年的時間里美國人對“文革”時期中國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的評說做一梳理乃至分析、評價。最終我發現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至少對我而言不是兩、三年的時間能夠完成的工作,因為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我始終還有每周8到12學時的英語專業的教學工作。
- 上一篇:建筑設計實習報告 2018/11/20
- 下一篇:2017年環境科學專業就業前景分析 201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