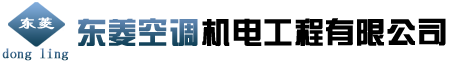傅慶軍:科技給押花藝術帶來無限遐想
2018/8/14 9:19:40??????點擊:
大年初一,微信群里,各種新春祝福和紅包此起彼伏。北林生態環保技術研究院合作工藝師傅慶軍的一組押花作品給群友們帶來別樣的祝福,這些作品畫面唯美、意境深遠。
軍營里的神槍手、第一軍醫大學的內科醫生、外貿公司的經濟師,轉眼,跨界押花大師傅慶軍已從事押花創作20多年。1990年,傅慶軍在華南農大梁承愈老師的影響下迷上了押花,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廣州市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的她常常利用業余時間創作自己的畫作。慢慢地,家里堆積的作品越來越多,她就拿著“無處安放”的押花作品去代銷,有時也拿著自己的作品去參加展會。她的押花作品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讓她倍感鼓舞。1995年,她出版了國內第一本押花專著《押花藝術》。后來,她干脆停薪留職,“炒”了國營單位的“鐵飯碗”,招兵買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作坊真樸苑,開起了實體店。1998年,真樸苑創作的押花長畫卷贏取了吉尼斯世界之最的稱號;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9幅參展作品又全部拿了世博會的系列金獎。經過前期的不斷探索前行,傅慶軍繼而把真樸苑注冊成了公司,組建了一支專業的押花創作團隊。在市場摔打的同時,她也沒忘記繼續押花學術的探索,不斷有專著出版。20多年來,傅慶軍追求押花技術創新發展的熱情始終未減。
押花藝術,是選取新鮮花草等植物,脫水后,依其天然形態、紋脈、色澤,粘貼成各種圖案畫面,然后進行真空覆膜或密封等處理,以保持其真實的質感和防腐防污,最后制成畫或各種工藝品。押花藝術離不開植物,但它不僅僅是植物處理和粘貼,在畫面造型中,蘊含著藝術家獨特的創作構思。因為每片植物形態都不同,所以制作的畫面形神無一相同。隨機巧妙利用材料,很能體現制作者的氣質和個性。
那么應該叫“押花”還是“壓花”?傅慶軍告訴記者,在亞洲的國家和地區都稱為“押花”,如日本、韓國、臺灣等,商業上也以押花相稱。而美國華人和大陸的學院派多稱“壓花”。但同時,壓花這個關鍵詞很早而且一直是用在指采用模具在革面壓出花紋或模擬某些動物皮粒,所以容易混淆,常有一些人在押花群里叫賣壓花機,鬧出不少笑話。傅慶軍認為,名字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沒有什么對錯,既然無法統一,那就百花齊放,順其自然,叫哪個都可以,為了便于網上搜索,我們兩個都一起用。
說到押花藝術,大概99%的國人會說沒聽過,可是追根溯源,這種植物粘貼技藝在中國已有千年歷史。只因原生態花卉難保存,歷史上除個別植物品類的工藝畫有商業經營,如始于隋朝的麥稈畫(現已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年成為搶手外銷貨的通草畫、棉花畫;此外就是只在乞巧、秋色的民間民俗活動里嶄露頭角的“梅花香”“瓜子燈”“谷花”等,歷史上對植物的粘貼技藝著實少有記載。也許是上蒼有意地保留了這樣一塊既特別貼近生活又圣潔高雅之地吧,這片處女地沒有條條框框,沒有標準,更沒有官話,只有自然想象發展的空間!所以,創新對于押花藝術來說,不僅沒有桎梏,而且如魚得水。所以押花是傳統向現代跨界延伸的藝術。
傅慶軍說,目前我國一些大專院校已開設關于押花的課程,但不管在國內還是相對盛行的日本、韓國、美國等地,押花作品都較少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大多都限于在圈子內“玩”,頂多作為展品出現在專業展會,或者就是制作簡單的書簽等小飾品在非常有限的市場里銷售。記者在淘寶上搜了一下,銷售成型押花作品的賣家確實很少,規模銷售的店家更是少之又少。
要靠這樣一個小眾商品來養活一大幫員工,著實不易。回望來時路,傅慶軍苦笑著告訴記者,如果還有回頭路,她打死也不會選擇這條路,太苦了,但她卻從來不曾后悔。不撞南墻不回頭的她也時常鼓勵身邊正在創業的朋友“堅持就是勝利”。
作為大陸較早接觸押花商業化的一批人,傅慶軍的堅持,更多的是因為肩頭的使命感。她說,如果押花作品僅僅停留在個人自娛自樂層面,它有可能會失傳,要讓它發揚光大,就必須走商業化道路。只是,當初的她不曾料及,做一個拓荒者會如此之難。
雖然從事押花藝術20多年,傅慶軍仍然謙虛地說,自己的押花水平還不成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她認為:“世界上的植物有幾十萬種,我們利用起來的就是一個零頭,而且只是很基礎的利用。再者,圖案的創作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科技的發展對植物的處理和保存也會有很大的推動,比如,我們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現代科技突破畫框的限制,讓押花作品也能成為那種可以貼在整面墻上的開放式的畫作。”
軍營里的神槍手、第一軍醫大學的內科醫生、外貿公司的經濟師,轉眼,跨界押花大師傅慶軍已從事押花創作20多年。1990年,傅慶軍在華南農大梁承愈老師的影響下迷上了押花,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廣州市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的她常常利用業余時間創作自己的畫作。慢慢地,家里堆積的作品越來越多,她就拿著“無處安放”的押花作品去代銷,有時也拿著自己的作品去參加展會。她的押花作品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讓她倍感鼓舞。1995年,她出版了國內第一本押花專著《押花藝術》。后來,她干脆停薪留職,“炒”了國營單位的“鐵飯碗”,招兵買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作坊真樸苑,開起了實體店。1998年,真樸苑創作的押花長畫卷贏取了吉尼斯世界之最的稱號;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9幅參展作品又全部拿了世博會的系列金獎。經過前期的不斷探索前行,傅慶軍繼而把真樸苑注冊成了公司,組建了一支專業的押花創作團隊。在市場摔打的同時,她也沒忘記繼續押花學術的探索,不斷有專著出版。20多年來,傅慶軍追求押花技術創新發展的熱情始終未減。
押花藝術,是選取新鮮花草等植物,脫水后,依其天然形態、紋脈、色澤,粘貼成各種圖案畫面,然后進行真空覆膜或密封等處理,以保持其真實的質感和防腐防污,最后制成畫或各種工藝品。押花藝術離不開植物,但它不僅僅是植物處理和粘貼,在畫面造型中,蘊含著藝術家獨特的創作構思。因為每片植物形態都不同,所以制作的畫面形神無一相同。隨機巧妙利用材料,很能體現制作者的氣質和個性。
那么應該叫“押花”還是“壓花”?傅慶軍告訴記者,在亞洲的國家和地區都稱為“押花”,如日本、韓國、臺灣等,商業上也以押花相稱。而美國華人和大陸的學院派多稱“壓花”。但同時,壓花這個關鍵詞很早而且一直是用在指采用模具在革面壓出花紋或模擬某些動物皮粒,所以容易混淆,常有一些人在押花群里叫賣壓花機,鬧出不少笑話。傅慶軍認為,名字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沒有什么對錯,既然無法統一,那就百花齊放,順其自然,叫哪個都可以,為了便于網上搜索,我們兩個都一起用。
說到押花藝術,大概99%的國人會說沒聽過,可是追根溯源,這種植物粘貼技藝在中國已有千年歷史。只因原生態花卉難保存,歷史上除個別植物品類的工藝畫有商業經營,如始于隋朝的麥稈畫(現已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年成為搶手外銷貨的通草畫、棉花畫;此外就是只在乞巧、秋色的民間民俗活動里嶄露頭角的“梅花香”“瓜子燈”“谷花”等,歷史上對植物的粘貼技藝著實少有記載。也許是上蒼有意地保留了這樣一塊既特別貼近生活又圣潔高雅之地吧,這片處女地沒有條條框框,沒有標準,更沒有官話,只有自然想象發展的空間!所以,創新對于押花藝術來說,不僅沒有桎梏,而且如魚得水。所以押花是傳統向現代跨界延伸的藝術。
傅慶軍說,目前我國一些大專院校已開設關于押花的課程,但不管在國內還是相對盛行的日本、韓國、美國等地,押花作品都較少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大多都限于在圈子內“玩”,頂多作為展品出現在專業展會,或者就是制作簡單的書簽等小飾品在非常有限的市場里銷售。記者在淘寶上搜了一下,銷售成型押花作品的賣家確實很少,規模銷售的店家更是少之又少。
要靠這樣一個小眾商品來養活一大幫員工,著實不易。回望來時路,傅慶軍苦笑著告訴記者,如果還有回頭路,她打死也不會選擇這條路,太苦了,但她卻從來不曾后悔。不撞南墻不回頭的她也時常鼓勵身邊正在創業的朋友“堅持就是勝利”。
作為大陸較早接觸押花商業化的一批人,傅慶軍的堅持,更多的是因為肩頭的使命感。她說,如果押花作品僅僅停留在個人自娛自樂層面,它有可能會失傳,要讓它發揚光大,就必須走商業化道路。只是,當初的她不曾料及,做一個拓荒者會如此之難。
雖然從事押花藝術20多年,傅慶軍仍然謙虛地說,自己的押花水平還不成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她認為:“世界上的植物有幾十萬種,我們利用起來的就是一個零頭,而且只是很基礎的利用。再者,圖案的創作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科技的發展對植物的處理和保存也會有很大的推動,比如,我們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現代科技突破畫框的限制,讓押花作品也能成為那種可以貼在整面墻上的開放式的畫作。”
- 上一篇:為什么說2016唐山世界園藝博覽會是一個好作品 2018/8/14
- 下一篇:由一場突然取消的花木展會所想到的行業問題 2018/8/13